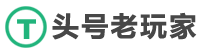有些沉重,带来的只是思考,不是泪水。就在前段时间很小姨子看了一部小电影,电影开头有一段良多和继子淳史的对话。
“为什么兔子死了你还笑呢?”
“因为很好笑”
“哪里好笑了?”
“因为怜奈说要大家给兔子写信”
“写信不错啊”
“明明没人看 但还要写吗?”
从一开始看到女儿在母亲身边打下手,儿子良多在赶回家的路上。炎热的夏天,大家齐聚一堂,老房子里,大家各怀心事,却也算得上其乐融融。气氛温和到,要不是因为我看见了遗像,我甚至一直以为,他们口中的在父亲偷西瓜时说话,一表人才的大哥纯平不一会儿就会出现。我像是第一次接触死亡,感到无比遗憾,却又很奇怪的并不痛苦。我难以想象失去长子的绝望,难以与微笑着聊天的母亲共情,她看起来好轻松,让我感到无比沉痛顿时失语。

良多说去扫墓,母亲笑着一起去了。我总觉得死亡是件需要避讳的事儿,或许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家人们闭口不提。母亲往大儿子的墓碑上浇上凉水。“今天一直好热 浇点儿水舒服些。”镜头转向淳史,我觉得他在强忍笑意,又像是费力读懂人们如此举动的含义。我同他一般觉得好笑,人们总献上自己崇高的爱意弥补原本的遗憾,本质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不再愧疚罢了。
扫墓路上母亲跟良多讲了个故事:“听说冬天没冻死的纹白蝶,到了春天就会变成小黄蝶。”
后面的一幕,一只小黄蝶在今日那晚飞进了老房子,母亲伸着双手在屋里追。母亲的延伸一定程度是令人恐惧的,说不上悲伤,像是癫狂。她说那是她的儿子。我紧张地注视着小黄蝶落到了纯平的遗像上。惊讶之余,从母亲脸上看到了对儿子的留恋。
“震慑我的不是蝴蝶的诞生,而是蛹的死亡。我因为被一群死亡包围而感到恐惧。”
纯平当年为了救一个溺水的孩子意外离世,可孩子活了下来。无奈孩子成为了一个庸庸碌碌的人,烦于生计。父亲感到愤怒,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废物牺牲自己优秀的儿子。母亲怨恨,每年忌日都请那个孩子来家里,以此增加他的负罪感。表面如何淡定,纯平的死都像是水中落石,等水花平静下来,也改变不了沉石的事实。
三年后,父母离世。良多带着妻子孩子扫墓,他像几年前的母亲一样往墓碑上浇水。我想起《法兰西组曲》里一段话:
“我们总是精心地替死人穿好衣服,为他们梳妆打扮,而他们也注定要在泥土之中腐烂的。这是最后的敬意,是对自己亲爱的东西所表达的至高无上的爱意。”
像他们这般全心思念故人,在那个时刻,纯平会在他们心中再次复活,轻快地走完了一生。就像我们总是给故人烧纸,他们收不到,可火是真实存在的,这旺盛的火给我们带来的温暖,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所以这烧纸,也本是为活着的人自己而烧罢了。
忌日第二天一大家人就散了,各怀着各的秘密与苦恼。人生的路上哪儿有时间怀念与修复啊,人生的路上步履不停。
有时候看电影不是看它能带给你多少的欢乐,而是要看着不电影给你带来了什么的启发,一部好的电影是令人感动,却不悲恸。有些沉重,带来的只是思考,不是泪水。